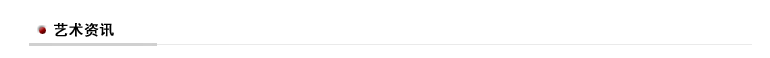|
一
十年前,与朋友编辑一部有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纪实摄影作品的汇集之作《中国故事》时,著名摄影家袁冬平先生推荐并拿来陈锦的一组《四川茶铺》,当下看着就喜欢。除了那些拍摄考究的黑白影像本身之外,我更喜欢图像当中显现出来的那种自在闲适的平民素常的生活。以我等久居京城天子脚下,过着每日为衣食奔命,看各种报刊上面义正辞严的重大话题,听出租司机蹬三轮的都在谈政治局人事变动的怪异日子,你就知道,作为一个平头百姓,我们离世俗正常的生活尚还远着。尽管彼时我尚不认得陈锦,亦未到过四川成都一走,但看那种恍若隔世自在自为的市井日子,你就会知道,四川成都一地的平头百姓真是早早回到了平头的位置上来,与我等跟国家政治的胶着状态不同了。
再次看到陈锦的作品,已经是这部集合了八百余幅照片的《市井》。影像自是繁复绵密,恰如他拍摄的市镇街衢的屋宇重檐,层层迭迭无以计数。陈锦将近二十余年的这些照片分门别类,然后旁涉历代关于成都一地的世俗图画,更有消逝不再的地方民谣,还有他本人关于此地风习历史掌故的仔细描述,各类角度各般表示相关参发,构成一片关于成都一带世俗生活的浩荡景观。9月3日,我赴成都,当晚参加了陈锦搞的一场图像演示活动。更多的照片编辑起来,配以地方戏曲杂以各类实验音乐,以动态投影的方式在一个叫作“皇城老妈”的大场子里折腾了半个多小时。端的是人头攒动议论纷纷灯光摇出一地的影子。场子外边一片竹椅子上欹里歪斜坐满了茶客,楼下火锅也在沸着。舍身这样一个与画廊、美术馆展场完全不同的热闹人群之中,看着那些影像的闪烁移动交替变换,听着有点儿妖狂怪异的音乐和各类方言说辞,你就会知道这些看客并非如我这样的外乡人那样充满了好奇和郑重。他们仿佛置身社火乡戏的场子里,看的不是我们以为重要的“摄影作品”,他们本身即是陈锦照片中的各色人物,他们只是在其中寻找自己的摇曳身段儿和生动容颜。
我看重的正这种浩荡繁复的世俗景观,原因在于我们与这种日子真是久违了。远且不说,三十年前,无论是京畿之地还是偏远乡野,除了口音略有不同之外,真也是一个头脑一种意识,大家谈的总是自上而下贯彻到底的一种话题一种声音。尽管国家幅员辽阔,又有山川江河阻隔,民族亦是多种多样,文化更是差异不同,但你在任何地方都会感受到上层政治意识无处不在的惊心动魄。何以能见到细致迥异自在自为的世俗生活样貌?何以有独特异质的地域化的风尚趣味?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末始,中国摄影一反这种统一政治意志的宣传和夸饰,开始关切到个人内在生活的私秘世界和底层民众的艰难日子。此种态度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渐成大势,比如于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关注,比如对现实生活的哲学想象和艰深表达。一时竟也群雄并起影像庄严。但这种以反政治意识形态宣传姿态出现的摄影,亦不过是以逆反的姿式表达出另一种充满精英意识的政治化的诉求。对重大主题的关注,对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等等大词儿的滥用,恰恰显示出来,我们仍然是在国家主义政治的层面上,来重新设定我们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尚没有将世俗社会生活的恢复和自为,看作是一个成熟、正常的国家所应有的样子。
自八十年代中期始,上层政权强调党政分离,国家与社会始有微妙的间隙。延至九十年代初时,也是一代人政治理想渐趋淡化,兼以改革开放重视经济生活的生长,中国百姓世俗化的日子才得以复原的契机与空间。至九十年代后期,政治化生活退缩至上层少数人群并趋于职业化。公务员制,党务人员,公共知识分子身份,成为政治体制运作及进行现实政治和文化批评的专业阶层。而平头百姓则不再与上层政治发生紧密的关联,寻常日子眼看着就过得有些个仔细绵密起来,渐渐有了各色的精致和丰富的细节。时有市井里弄村野乡镇的喧哗,也有家庭生活才可体会到的简静绵密。而且这种喧哗是大家心中久违了的俗民群众式的热闹,就像是过节之时社火乡戏里的人山人海,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人声鼎沸,饱满且有元气。这样的一种变化,就好比是久病的汉子渐渐体力恢复过来,走出门去,凭栏远望,看桃花儿开处车马络驿于途且有人声胡乱歌唱,于是面有喜色,眼瞅着就有了一种精气神儿,忍不住地摩拳擦掌,准备要做做什么事情了。这和当初被谁人组织鼓噪着到广场去热泪盈眶,不是一个意思了。
陈锦新作《市井》中的图像,其实就是丰富地展现了这番世俗景观复原之后的人声鼎沸与自在安逸。我看它的好处,也正在于通过这些影像的表征,告知我们,人的日子总算是回来了。长远地打量过去,你会发现,所谓的世俗景观,其实是活生生的多重实在,端的是无法引导和为国家政治所一直左右的一种自在自为的景观。就好比是青草生于河岸,总是自然而然之事。虽然不时会为人割刈翦除,日子长了,仍然是要萋然伏仰,成一平阔烂漫的风景。说得远些,上层政治端在上层,与黎民百姓的日子其实关系不大。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其实就是指的这种分殊真也是不好弥合。执意要庶民天天学文件领会上头的意思,让百姓登上大学讲台批儒评法从《水浒传》里看出投降来,与世界各国谈外交事宜,管理诸般国家大事(这种怪异的现实我们见得还少吗?)看着倒像是平民真正当家做了主人,有一种扬眉吐气改天换地的万千气象,结果却是国家也尴尬,百姓更是浑身不自在。社会层面的市井世俗自有世俗的无穷乐趣和猎猎风光,在主流人群看来仿佛是边缘化的存在,自世俗的视角看过去却无所谓什么主流和边缘。它其实是一条无所谓主次的大河,由不得你去围追阻截改道疏通。自这河流之央驾舟而下,一路看着两岸的山河大地,听着不住的鸟鸣猿啼,知道这俗常的世界亘古未变,心中生出无限喜悦,能够平然安静地生活下去,这其实已经足够了。
二
有人说陈锦影像作品的意义,多看重对那些川中平原富庶之地人文景观的图像表达,要处在于显现出中国文化的延宕和丰富性。我看这是瞎起劲。要说文化的样貌只在于那些世俗景观中的古旧破败和久已消逝的生活方式,拿这番说辞推动一下旅游事业,倒也没有话说。但要说这些世俗景观的恢复正是文化的接续和延展,说得这般重大紧要,我看与此前那种以反政治宣传为标榜的精英姿态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不喜这种牵强重大的话辞,再说了,这也真是小看了世俗的浩荡与壮观,怕是让世俗中人听着要笑起来了。
的确,除了那些动态鲜活的世俗生活的影像表达,陈锦的《市井》当中集合了大量西南四川成都一地的人文地理景观。那些逶迤幽静的小镇街道,那些青瓦覆盖鳞次栉比的房舍屋宇,那些陈旧落后的家用物什,那些环绕村落蜿蜒而去的清净河流,参天古树掩映下的古渡轻舟和缭绕村落之上的炊烟,构成一幅幅远离尘嚣世外桃园式的遥远风景。陈锦当然对这些诗意的风景,对市井平民那种缓慢变化的生活样态充满了迷恋和欣赏。这从它近二十年前拍摄的《四川茶铺》当中即可以看得出来。到了成都,陈锦挑了时间拉了一干朋友开车西去一个小镇,执意要大家在一个江边的茶铺坐坐。又与他一起赶场,听他边走边谈他的童年记忆,谈他当年在成都市内拍摄的这种由老虎灶、竹器桌椅、朴素的茶具和新鲜廉价的清茶、以及摆龙门阵的老人和大声喧哗构成的茶铺,如今已经变成了装饰堂皇非寻常百姓可以消费得起的茶楼,而只能在这样边远的小镇尚可以见到。他的口吻当中充满了往日不再的怅惘和怀旧情绪。他的年龄和丰富阅历,让他真切地看到了这种世俗生活的促迫中断与重新回来,更让他看到了这种充满人际温情和诗意化栖居的生活样态正在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迅速地消逝远去。作为一个摄影家,那些风景和生活样态是他赖以热爱活着的有限岁月的一个精神的寄居之地。正是积二十多年的四处游走、探访观看、影像的抚摸和一路怜惜,让陈锦的这册《市井》成为一曲喟然叹息的挽歌。
陈锦《市井》当中表达出来的这种叹惋当然不是孤立的。近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纪实摄影,特别是九十年代初以来的中国纪实摄影实践,一个极为重要的关切方向,即是通过影像来记录和描述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与乡村的复杂关系,从而构成对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现实的视觉表达。
他们的视线一方面集中于城市,侧重于关注表达中国城市化进程当中必然产生的剧烈社会冲突和新一轮的阶级分化。我们看到,在新闻摄影及其传播的视野里,急切的经济发展欲求、贪婪的财富扩张、体制多样交互作用及全球化经济发展背景之下的中国现实,表现为令人振奋的经济持续增长、国人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和国力的日益强大。而在社会纪实摄影家们的视野当中,他们看到的则更多是这种繁华背后隐藏的社会问题:大规模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现实境遇;大批因为城市改造和地产开发失去家园沦为城市贫民;人的精神价值及道德标准的沦丧缺失;城市化进程带来的财富增长更多地聚集于少数人之手;新的贫富差异不断产生新的阶级分化和敌对犯罪,等等,等等。我们在张新民的《包围城市》,赵铁林的《海南妓女》,吴正中的《波螺釉子路》,任锡海的《崂山大院》,王军的《城市边缘的孩子们》,牛国政的《梦境》、《练功者》,王福春的《火车上的中国人》,彭祥杰的《流浪大棚》,宿志刚的《废弃的工厂》,余全兴的《老城厢》,王耀东的《上海》,赵建民的《宠物》等等纪实摄影专题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现实焦虑和社会冲突的影像表达。
另一方面,则将视线集中于乡村,侧重于表现了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给乡村带来的新的危机和长远忧虑。这些纪实摄影家们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以丧失更多人的生存权益和迅速消耗更多的资源为代价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不平衡,不仅导致大批土地沦为城市发展扩大吞食的对象,同时也导致了资源的迅速馈乏和迫使乡村沦为城市发展的污染区域。牛国政的《小煤窑》,卢广的《艾滋病村》,路泞的《水泥厂》,井广平的《我的1998》,余全兴的《贫困母亲》,姜健的《主人》,颜长江的《长江三峡》,袁冬平的《穷人》,等等,都以令人震惊和内涵丰富的影像在这一向度上作出了有力的表达。
陈锦的《市井》则选择了另外一个向度,即将触角深入中国少数民族和边远小镇及乡村,以大量残余或者说幸存的人文地理景观作为他们的影像描述对象。同样的关注角度,如李玉祥为《乡土中国》系列图书所作的大规模的影像采集,张新民的《流坑》,黎朗的《凉山彝人》,晋永权的《傩》,吴家林的《云南山里人》,徐晋燕的《云南故事》,董建章的《绍兴水乡》等等,都是在这一向度上作出的影像努力。
或许我们会认为他们的这种影像关注方向没有直接地面对中国的现实境况,没有像前者那样关切到乡村平民生活背后的艰辛与苦难,或许我们会质疑他们的影像是否秉持了纪实摄影寻求表达客观真实的道德立场,甚至我们还会诘难他们的影像营造出一种过度诗意美好的景象。但是我们会发现,正是这种基于内在经验的个人立场和主观化的言说,构成了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纪实摄影的重要延展和深化表达。当初的纪实摄影那种强调“边缘记录”和“客观纪实”的理念,已经让位于“作者记录”的立场。重要的不再是影像与客观真实的重合,重要的也不是什么艺术。重要的在于,摄影家能否通过自己的影像描述,对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给出自己独特且有建设性的判断与表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陈锦的《市井》以另一种视角介入了对当下中国的现实关注和社会评判。他知道这些与他的个人经验紧密相联、承载着他丰富细腻的温情记忆和理想生活方式的美丽风景及生活样态,正在城市向乡村的大规模推进过程当中迅速地成为过去。作为一个摄影家,他无法阻止这个结果的到来。唯一可以做做的事情,只能是以一种迷恋既往和怅然怀旧的影像趣味,以一种若有所失的乡愁式的情怀,来表达自己对即将因城市化进程而迅速逝去的人际温情和诗意化栖居的叹惋,同时也表达自己对中国现代化/城市化前景的深切忧虑和强烈抵触。这种回望乡村,回望充满温情和诗意生活方式的现实逃避,就像九十年代初以来美术界“新文人画”思潮中的画家们回望古人的生活趣味一样,本身就成为他们不认同这种粗暴的城市化过程和目标,并且积极介入现实批判的最后的一声呐喊。
三
检视近二十年来中国纪实摄影家的操作方式,早期多有跑马圈地的嫌疑,而且多涉弱势群体及边缘人群,于普通常态的民众生活关切却少。这其中当然有为着引人注目的意思在。通常做法是,选取别人未曾涉及的题材范畴,主题先行,有点儿类似命题作文,然后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图像的采集工作予以完整的视觉表达。其最终的目标,往往是诉诸一个展览或者是一本画册。其图像采集的基本结构思路无非两点:一是如报道摄影那样,以线性叙事的方式展开图像叙事的逻辑。这样的视觉表达,规模较小者,多见于图片故事的体式,图像之间有着较为紧密的从内容到视觉形态的关联补充,有点儿像是文章的起承转合。较大规模的纪实摄影专题,亦类似图片故事的放大版,不同的是,更强调图像的独立封闭的表达功能,图片之间的关联较为松散。在这样的专题描述过程当中,每一图像分别展示与主题相关的细节信息,图像之间在内容上相互补充,而在视觉形式上强调变化和差异性。这样的一些图像集合于一体,共同完成对一个事件,一类人群,或者一个地域景观的系统化的视觉描述。我们在袁冬平的《精神病院》,孙京涛的《幸福路》,吕楠、杨延康、黄新利的《乡村天主教》,侯登科的《麦客》、张新民的《包围城市》,晋永权的《傩》,黎朗的《凉山彝人》,牛国政的《监狱》、《小煤窑》等等文本当中,都可以看出这样的构成关系。另一种结构样式是,先行选取一种图式,以此统一的视觉样式采集来自不同场景中的与主题相关的内容图像,以合并同类项的图像结构,强调图像的规模集合,来表达同一个主题。这样的图片集合会有相当强的风格化倾向,图片与图片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平行的关系。好处是图像的视觉样式高度统一,不好处是略嫌单调,缺乏叙事的灵活性与变化。国内摄影家及其类似文本,如肖全的《我们这一代》,姜健的《主人》、王福春的《东北人》,胡杨的《上海一家人》、宋朝的《矿工》,阿音的《蒙古人》等等,基本上都是采取了环境肖像的方式,集合相当规模的风格统一的图像,来表达相关的主题。
陈锦的《市井》结合了这两种纪实摄影专题的叙事结构样式。线性展开的叙事维度,采取了分单元的结构样式,列有寻梦,蜀犬吠日,街坊、家事,赶场,生意经、市民玩、茶铺、戏班子诸元。通过不同单元的差异性组合,分别涉及到他选取表达的市井生活的各个方面。然后再横向作图像的细节陈述和丰富铺陈,将种种与此单元相关的采集自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相关内容的图像合并在一起,来共同支持这一单元意欲表达的内容。
这一方式类似于1955年斯泰肯策划的《人类之家》大型展览的结构样式。好处是结构单纯清晰,其间细节丰富绵密,种种事物,各地场景的相关经验一一罗列眼前,端的是亦奇亦怪,叫人叹为观止。不好处,却是因为在此单元当中的相同内容,甚至相同样式的图像从左到右的罗列铺张组合,构成的却是一个平面化的表达。尽管有文字的精彩描述及历史的钩陈关联,并有成都民谣的间杂补充,但他在展现这一单元的相关内容时,却因没有纵向的视觉描述而挡住了更为丰富的细节。
这种表达的平面化还在于,陈锦有意地略去了图片内容发生的具体地点及时间的说明。仿佛这些密集的图像中所呈现的事物并不是特定的时空中的存在之物,而是从来如此,亘古未变,超越了时空的移易延宕。我们会看到,那些民众面孔、生活场景、宗教仪式、屋舍建筑、江上行船、街道景观、日用家什、各行百工、贩运买卖、茶铺饭馆、娱乐休憩、求签问卜,一切仿佛既成已久,凝固了一般。这些细节绵密丰富至极的图像,向我们显现出成都周边之地民众安逸超脱的生活状貌和奇异独特的风物。陈锦通过采集和组合这些独特的地域性生活符号,构成一种过度奇观化的异域景观。他过度强调了这种生活样态的地域性和不变性,夸大了这种异质性,但它却有意回避了这种生活样态的流变性和同一性,即他将成都一地的市井生活从中国当下现实当中抽离了出来,从而将成都一地世俗生活样态营造成一个暗合了我们想象的奇异图景。
有人说,这也是一种特别的视角,固然不错。但自这样的视角看过去,其实只是一种表面化的,甚至是概念化的世俗市井的浮华面目。他止于这种世俗的平面化的甚至夸张性的描述,其中没有问题,没有质疑。它更多的是通过集合这些安逸悠闲的市井图像来显现自己的欣赏趣味与价值认同。在这一点上,《市井》有着陈锦相当主观化的表达的一面。它更像是陈锦以及我们理想当中的所在,而不是现实本身的样态。《市井》如同一面浮世绘,为我们营造出了一个世外桃园般的景观。我们从中看不到世俗市井与国家政治的微妙关联,叫人感受不到政治对于下层市井俗众世界的辖制干扰,见不得国家于民众的种种约束,仿佛民生从来都是这样的宁静恬淡怡然自得,仿佛中国的市井社会从来就是这样的繁华似锦百变不惊。可是,对于中国的现实来说,世俗哪里是孤立自为的世俗民间?国家政治于世俗生活的影响,真也是风吹草动。可我们从中哪里能够看得出这样的风吹草动?远的不说,那些残酷的经验相去不远,回头想想,四十多年前,上层政治延及世俗,几经荡涤洗劫之后,平头百姓失去了世俗的生活之后,面对上层政治的迷惑茫然,不知如何自处的尴尬与难堪,真是历历在目。世俗已经是最底限的生活样式,再要洗劫世俗仅有的一点生机,叫这世俗中人怎么活得下去?所以陈锦《市井》当中对于世俗样态的欣赏和迷恋,或可看出我们于此自为的生活真是久违后的饥渴,但这世俗的样子其实也是几经荡涤洗劫之后的新芽初发,谈不上亘古未变。将这样的图像从动态的关联当中抽离出来的结果,其实也就成了一种于当下现实的遮蔽和误解。明白这些,其实再看这世俗市井之间一点儿民众的自得其乐,也真是叫人心酸不已。
任何语言形态的叙事方式――无论是文字表达还是影像呈现,都是赋予无限丰富杂乱的现实世界的一种秩序化的也是简单化的描述。无论何种语言,都不仅仅是对于现实之物的描述,而是建构出一个新的语言形态的存在,创造出一种符号形态的存在之物,通过传播平台以为那些不在场的人们所感知了解。尴尬的是,图像构成的这个表达本身,最终构成了一个与现实真实无关的新的体验王国,用鲍德里亚的话说就是,它成为一个更具影响力的“超真实”的存在。我们会因为《市井》这种文本当中显现出来的那种作者的主观倾向和激赏这种世俗生活的趣味而认同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成都人生活的安逸已经成为我们外地人的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想象。而这样的图像构成的视觉景观又在不断地强化和丰富着我们的这种想象。我们甚至会按图索骥地到成都一地去寻找这个文本当中展示的景观。我们甚至会更加相信这个图像文本当中集合而成的景观,而对那些异质的现实景观置之不理。这样的文本不再是指向它表达的事物,它本身即是一个充满无穷魅力的事物。它甚至超过了现实__四川平原市井世俗景观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它在我们的眼前置换和替代了那些世俗现实生活本身。正如鲍德里亚所说:“影像不再让人想象真实,因为它就是真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影像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的表达样式,它掩盖了现实,并使现实消失在这种表达的过程当中。这一点,或可看作是语言本身的无奈和尴尬。但如何控制使用影像语言,如何以更为准确的视角去超越语言的有限性,以接近对象世界的真实表达,这不仅是陈锦作为一个摄影家面临的困难,亦是中国当代纪实摄影家们共同要去着力解决的问题。 |